近二十年來國內論說語篇研究綜述
更新時間:2023-08-25 12:05:00 高考知識網 www.pvszdiiu.cn摘 要:本文從界定、宏觀結構、微觀結構和二語教學等四個方面對二十年來國內論說語篇的研究進行梳理。我們發現,隨著研究不斷深化與細化,在結構布局與修辭特點、主位推進與語篇銜接、技能教學與語言要素教學等方面取得一些成果。然而,由于理論創新性不足,定量與實證研究不夠,因而本體研究、對比研究與二語教學研究有待進一步提高。
關鍵詞:論說語篇 宏觀結構 微觀結構 二語教學
一、引言
論說語篇(亦稱議論文、論述文、論辯文)主旨是論說,發表議論,闡明事理,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21世紀前,學界多關注論說語篇概念、類型、構成要素、論證方法等的研究,多囿于結構主義視角。21世紀后,學界不斷探討論說語篇的結構布局、微觀結構、第二語言教學、漢外對比等方面的研究,借鑒認知語言學、系統功能語言學等理論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且研究不斷細化,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試圖從界定、宏觀結構、微觀結構、教學等四個方面對二十年來論說語篇的前人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歸納,以期有助于漢語論說語篇研究。
二、論說語篇界定
(一)內涵與要素
論說語篇是文體類別之一。張壽康(1985)認為議論文是用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表達主旨的,主要運用議論的表達方式,它要求論點鮮明,概念準確,論據充實,論證嚴密,論述時說理充分,實事求是[1]。論說語篇的實現包括口頭與書面形式,如辯論、演講、討論等和各類評論、科學論文、政治論文等分屬口頭和書面論說語篇。牛殿慶、周采霞(1996)分析了議論文與文學作品中論說表達方式的區別,前者是作者通過對事物的分析評論闡明觀點的表達技巧,后者是和敘述、描寫、抒情緊密結合、互為依附表露作者的表達技巧[2]。
關于論說語篇的構成要素,主要觀點是“論點、論據、論證”議論三要素說,由陳望道(1922)提出[3],至今還在沿用。后人對議論三要素也有許多爭論,如孫彥杰、韋丙海(2002)認為議論三要素理論是一種簡單的、直線式的、單方向的證明模式,不利于創造性思考能力的培養與訓練[4];尹相如、劉欣(2004)認為論證是作者用論據證明論點的過程,旨在把?點與論據之間的內在聯系揭示出來,因此論證并非實體,不能視為要素,而是論點與論據之間的連接方式,正由于連接方式的不同,產生各種各樣的論證方法[5]。
不少學者提出其他觀點,如謝志禮、王黎靜(1999)將議論文構成要素分為淺表要素和深層要素(或稱外在要素、內在要素),前者由論題(第一實際要素)、論點(統帥要素)、論據(基礎要素)、結論(終極要素)四個要素構成,后者則是指構成議論性文章的核心的內在要素??論證[6]。王鳳英(2005)采用亞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式法(大前提、小前提和結論),將論說語篇分為三個部分:論點、論證和結論,其中論證包括論據和論證方法[7]。這些研究依然局限在結構主義框架中,未能從功能角度進行深入分析。
(二)類型與特征
張壽康(1985)依據語篇的社會功能將議論文分為:政治性專論、宣言、聲明、社論、評論、講話稿、決議、會議紀要、按語、科學論文、雜文等類型[1]。方武(2003)從系統功能角度將論說語篇分為三大類:議說型、說明型、論證型。論證型中又細化出邏輯推理論證型和綜合論證型[8]。但不同類別論說語篇的特征研究較欠缺。
論說語篇的特征。郭兆武(1997)認為論說語篇具有內容的理論性、結構的邏輯性、表達方法的論說性、語言的抽象性等特征[9]。王鳳英(2005)認為論說語篇的特點體現為話語的目的性、各個判斷之間的語義關系、謀篇布局和語言表達式,其中目的性及語義關系決定謀篇布局和語言特點[7]。曾常紅(2007)則從語篇性角度分析了辯論語篇特征:在人物/角色的態度、觀點上表現出強對抗性,不同人物/角色的立場相對相反,在話語信息交流上表現為互動性,不同人物/角色的言語行為有應變性,在結構形式上因具體論辯形式或辯論規則不同而有所調整,但從總體輪廓上說,不外乎“提出問題-分析、論證論題-得出結論”的結構模式[10]。以上研究未能充分探討論說語篇的“語篇性”特征,研究概括性還較差,未能提煉出可驗證性要素進行有效分析。
(三)論證內涵與方法
論證的說法很多,有過程論、層次論、方法論、結構論等。如郝赤(2003)認為論證是統合技巧,即統合了諸如句法、詞法、語法、修辭法、邏輯法、章法等方法,從內容上看主要包括概念說明、論據證明、分析闡明,從形式上看主要包括巧設理群、論點有襯托、詩意論證;并提出論證的特點主要有:具有議論的起始、大小層次階段,并有明確的中心句;具有最能說服讀者、最能為中心論點服務的議論過程大小層次安排;語言須適應議論語體及語境要求,體現出立論的證理風格、駁論的辯理力度[11]。
關于論證方法,何應燦(1988)認為論證方式是指論證過程中論據與論據,以及論據與論題之間的邏輯聯系方式,也即是論證過程中用論據推出論題的一系列推理方式的總和[12]。何武(2001)、郝赤(2003)和王鳳英(2005)論述了論說語篇的論證方法,何文歸納為歸納法、例證法、喻證法、引證法、反證法、排它法、比證法、二難法[13],郝文歸納為歸納法、演繹法、總分法、遞進法、比較法、思維抽象到思維具體等六種[10],王文歸納為直接論證和間接論證,直接反駁和間接反駁,演繹論證、歸納論證和類比論證[7]。王壽沂(1995)提出要巧用“比喻說理”的論證方法,即利用事物或事理之間的相似點,把本體、喻體及其相似關系顯示出來[14]。趙書勤(1997)則歸納為形式邏輯的論證和辯證邏輯的論證,前者又包括事實論證和理論論證,是論證邏輯性的基本保證,后者是從全面材料出發,分析事物相互矛盾的各個側面,找出主導方面,找到轉化條件及存在依據,得出初步結論[15]。這些研究角度多樣,分類繁雜,缺乏一種形式與功能相驗證的分類模式。
三、論說語篇的宏觀結構研究
(一)結構布局
廖秋忠(1992)認為“論證結構”可以作為識別論證體的形式標準,論證結構是根據篇章中各個組成部分的結構關系和它們的功能確定的,若處于同一層次的兩個語段之間存在著論題與論據的功能關系,便構成了一個基本的論證結構,包括論題和論據,還有引論和結尾部分[16]。這一界定對論說語篇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據不同標準,進行結構布局的研究。如王鳳英(2005)認為由于交際目的、論說場景、論說對象等不同,論說語篇的布局結構會發生變化,可分為完全結構論說語篇和非完全結構論說語篇,后者包括無論點論說語篇、無結論論說語篇和泛論說語篇[7]。洪明(2005)將論辯語篇歸納為一般-具體型、主張?反主張型和問題?解決型等三種語篇模式[17]。李躍進(2008)認為論說語篇的基本結構形式是“引論?本論?結論”(即“總?分?總”方式)、“分?總”、“總?分”、中心論點中置式三種變化形式,分論點之間的關系可以是并列式和遞進式兩種[18]。
(二)修辭特點
論說語篇具有獨特的修辭特征。如羅娟姣(1998)認為論說文的修辭特點包括選用正式的文體;注意句子的結構與排列,交替使用長、短句,注意圓周句和松散句的合理搭配;避免使用被動語態,多用主動語態;選詞時力求簡單、準確、有力;巧妙地使用反復、排比、反問等,產生突出的效果[19]。段李敏(2007)將修辭論辯界定為演說中演講人在不確定條件下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合理維護的言語實踐,目的在于說服聽眾,促使其采取行動,其主要特點有:修辭論辯需考慮論辯者和聽眾的社會、政治、文化、倫理、心理等諸多因素,具有不確定性;修辭論辯建立在“或然性”或“可能性”基礎上,研究的不是必然的真理,而是具有可能性的見解或主張;修辭論辯要求論證的是具有社會意義的事情;在修辭論辯中,語言手段的主要功能是說服,而不是美化和修飾[20]。目前研究多舉例說明,也較零散,欠缺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
學者還從思維模式角度對比英漢論說語篇的修辭特征。如胡曙中(1993)引介美國學者R.B.Kaplan的語篇修辭模式,認為英語語篇的思維模式為亞里斯多德線條式,而漢語是迂回式;英語語篇的組織和發展呈直線型,漢語語篇則呈螺旋型發展[21]。許力生、李廣才(2002)借鑒Kaplan的研究,對比發現漢語和英語不僅在銜接手段使用上側重不同,而且在語段發展模式分布上也存在差別,如英語段落多使用發散型,漢語段落多使用延續性和發散型;英語較多地使用照應,且主要是名詞照應,漢語語料則更多地使用重復和省略[22]。夏莉(2006、2007)分析了英漢論辯語篇的修辭特征,認為漢語作者比英語作者留給讀者的空間更大,英語作者在論辯語篇的寫作中傾向于清晰地表明自己的觀點、看法和立場;漢語作者在論辯語篇的寫作中比英語作者更喜歡引經據典;漢語和英語都相當重視在論辯語篇寫作過程中適應讀者的信息需求,以取得讀者共識,達到成功勸說的目的;漢語作者越來越多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因此漢語作者在論辯語篇的寫作中交錯使用不同的修辭模式[23];英語多采用演繹型論證方式,漢語多采用歸納型和半歸納型,即論點往往隱藏在文中或末尾處,由讀者揣摩作者的寫作意圖;漢語運用的論據種類比英語的豐富,漢語的組內差異也比英語更加明顯;漢語更加注重在感情和情緒方面引起讀者的共鳴,理性訴求使用少于英語,都同樣關注倫理訴求[24]。
討論具體論說方法與段落結構的主要有:劉穎(2004)從論述焦點、問題解決類型、問題討論類型三個方面對比了中國大學生的母語作文和英語作文的修辭策略,主要表現在:英語和母語作文均以問題為中心,前者多采用原因分析型和解釋型的方法分析問題,后者多采用個人的解決方法和解釋型方法分析問題,以上不同原因在于文化差異,以及運用母語寫作的訓練方式[25]。劉朝彥(2006)從統一性、連貫性與完整性對比討論了英漢論說文的段落,認為典型英語段落結構是主題句加擴展句,段尾還有和段首主題句呼應的結尾句,漢語的段落結構主要體現為螺旋思維程式;英語段落較多地使用照應與連接詞語,漢語段落更多地使用省略和重復;英語段落通常可分出主題句、擴展句和概括句,漢語段落結構的完整性往往不在一個自然段中體現出來,只有當幾個自然段聯合起來時才能闡述充分[26]。
四、論說語篇的微觀結構研究
(一)主位推進
這方面的研究多舉例,分析尚待提高。如賈燕梅(2007)通過一篇議論文的實例分析了論說語篇的主位和銜接,探?了議論文語篇的復雜性及獨特性[27]。趙瑞(2009)認為小句主位可快速把握文章的組織結構;主位推進模式可大致看出文章前后段落的銜接和連貫程度;再通過銜接手段深入分析語篇的篇章性;最后從語言層面上進行評判,詞匯的選擇、拼寫、語法等微觀方面來把握[28]。蔣旭峰(2007)借鑒邁克爾?休依提出的情景?問題?回應?評價模型,分析了經管類論說型文體的主位推進模式,認為連續型、簡單線型、自由T-R型等主位推進模式最常用[29]。
(二)詞匯銜接
研究多集中在英語論說語篇上。如陳芳(2008)認為英語論說語篇的詞匯銜接發展模式主要體現為:詞匯銜接手段的使用頻率呈現出簡單重復>義關系>復雜重復>上下義關系>反義關系和部分整體關系,并且隨著年級的上升,簡單重復使用的頻率呈下降趨勢,但是其它詞匯銜接手段的使用頻率都呈上升趨勢[30]。余娜(2007)討論了中國大學英語議論文中因果連接詞的使用情況,認為中國英語學習者使用因果連接詞的頻率總體大大高于本族語者,因果連接詞通常位于句首,而較少放在句中;因果連接詞的使用頻率與寫作質量幾乎沒有相關性,而中國英語學習者使用因果連接詞的豐富性與寫作質量是密切相關的;因果連接詞的使用可能受母語遷移、教材與教師的指導和文化因素的影響[31]。這些研究對推動二語教學有著重要作用。
(三)英漢語篇銜接對比
研究多集中在顯性銜接上。汪清(2007)統計分析英漢議論文體主位推進模式頻率,總結出:英漢議論文體的主位推進模式主要是行型、集中型和延續型;跳躍型小句的數量在英漢語語料中呈顯著差異,漢語語篇更講究起承轉合[32]。馬巖峰、鐘竣琳(2008)對比分析了英漢寫作中論述視角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在主體視角上,漢語傾向于用第一人稱復數形式“我們”來代替自己抒發觀點、表達意見,而英語則傾向于直接用第一人稱“I”毫無顧忌地闡明自己的觀點;英語物主代詞的使用頻率遠遠高于漢語[33]。張愛雄(2010)考察發現英漢顯性銜接率分別為89%和79%,說明漢語不因重意合而顯性銜接率低,英語也會省略一些連接性詞語;不同的是漢語論說語篇顯性銜接率不衡,而英語則比較衡[34]。
五、論說語篇的二語教學研究
(一)教學理念
研究重在語篇結構,關注教學理念的分析。如郭兆武(1997)從選題、立論和取材三個方面討論了論說語篇的教學,認為要根據需要和可能選題,要確立正確的觀點,從自己生活與知識的倉庫里選出能充分有力地證明自己觀點的各種材料,根據論證對象安排好觀點與材料的先后次序,安排好各分論點及其材料的次序等[5]。王德慶(2008)認為以“論”的教學體系重在讓學生了解議論文的基本知識和主要形式,解決了議論文的模式和規范,但容易將議論文教學引向僵化,走入死胡同,在此認識上,他提出以“理”的新的教學思路,使學生更注重在作文說理內容和內涵方面的挖掘,解決怎么寫好的問題,有助于開拓議論文的深度和廣度。因此,初級階段可主抓議論,高級階段可主攻議理[35]。
(二)閱讀教學
關注實證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鄒啟明(2000)通過對中國大學生閱讀英語論述文的分析,指出達到中高級語言水的學生在閱讀語言難度中等、結構基本順暢、主題熟悉的英語論述文時,會根據文章結構做出必要的在線關聯推論,建立起命題之間的邏輯關系,并以此來組織自己的思維表征,在此基礎上指出語言能力和結構知識的確是影響第二語言閱讀的重要因素[36]。鄒啟明(2001)實驗分析了論述文篇章處理模式對語篇理解的影響,證明了第二語言閱讀與第一語言閱讀一樣存在由下至上、由上至下和綜合處理三種模式,采用綜合處理模式的受試者在閱讀記憶方面明顯優于主觀處理者和消極處理者,是第二語言閱讀中最有效的篇章處理模式;在此基礎上,提出在第二語言閱讀教學中可將母語閱讀技巧轉移到第二語言閱讀中去,積極運用自己的背景知識,結合文章命題的邏輯結構進行思維,達到提高閱讀理解和記憶的目的[37]。鄒啟明、童冰(2002)引介Meyer(1983)的頂層結構理論,將論說結構分為因果結構、比較結構、描述結構、反應結構(或問題?解決結構)和集合/時間順序結構五種,通過實驗分析得出不同頂層結構對外語讀者的書面記憶影響不同,不同母語的讀者對各種結構的敏感度不同,運用頂層結構來組織書面記憶的外語讀者在信息記憶方面明顯優于不用文章頂層結構的讀者[38]。
(三)寫作教學
開展統計分析,指出存在問題,提出相關建議。如吳婧(2003)以Kaplan(1966)“英語段落呈線性發展”為理論框架,調查了中國大學生英語論說文語篇結構特點,認為中國大學生英語論說文的語篇結構明顯具有漢語“迂回型”和“靈活型”語篇模式特征,他們所寫的篇章主題句與英語語篇預期的篇章主題句存在差異,缺乏概括性和拓展性,同時中國大學生不擅長用段落主題句預示段落內容和發展趨向,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在英語寫作初級階段加強論說文語篇結構特點分析的重要性[39]。呂欣(2006)從超結構、圖爾敏的非形式推理分析模式以及勸說式呼告這三個方面分析了非英語專業學生英語論說文中存在的問題:文章結構的不完整,邏輯思維不強,推理不深,缺乏具體和權威的論據材料以及相應的正當理由或根據,很少使用勸說式呼告,以及文章缺乏說服力[40]。吳小林、吳雪穎(2006)從語段的布局謀篇方式和句子的銜接手段綜合考察了中國大學生在論說文寫作中語篇連貫性存在的問題:語篇的布局謀篇方面呈現典型的東方模式,其行文發展呈螺旋式結構;在銜接詞的使用上普遍存在銜接詞數量多,種類單一等問題,由此提出應將語篇教學法納入時教學,從整個篇章布局結構著手,分析句際、段際間銜接關系[41]。陳明亮(2013)認為論說文開篇段落的深層結構由現實、理想、主題和價值四個成分及其問答關系構成,可通過選擇表述的起點和順序、中心問題、顯性或隱性的表述方式等轉化為表層結構,形成寫作思路,從而進行論說文開篇段的寫作[42]。
(四)詞匯、句式教學
對論說語篇中語言特征進行研究,多集中在情態動詞和疑問句等方面。如王文倩、沈永杰(2008)分析認為中國英語學習者在情態動詞的使用數量方面存在過度的傾向,而在使用種類方面存在過窄的傾向,語氣較硬的“can、should、will”使用較多,相對委婉的“would、could、might”使用較少,這與英語情態動詞的特點、學習者的理解能力、教學不足等有關[43]。王立非、張巖(2006)對比分析了中外英語學習者英語議論文寫作中疑問句使用的特點,結果表明:中外英語學習者使用疑問句的數量超過本族語者;二語學習者在三個部分的疑問句分布差異顯著,即正文中出現最多,開頭其次,結尾最少;中國低年級學生使用疑問句多于高年級學生,低年級使用最多的疑問引導詞是“do”和“be”;中國學生使用疑問句的主要功能表現為話題導入、語篇限定、重點強調和銜接與連貫4種功能。這表明二語學習者存在過多地使用疑問句的傾向,這就要求在寫作教學中應對學生加以引導[44]。
六、結語
本文從論說語篇界定、宏觀結構、微觀結構和二語教學等四個方面對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研究不斷細化、深化,然而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論說語篇理論研究多借?西方理論,本土理論的創新不足;第二,偏重借鑒西方理論進行論說語篇的二語教學研究,本體研究相對不足;第三,論說語篇與其它類型語篇的對比研究明顯不夠;第四,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研究不夠;第五,二語教學研究較粗淺,多停留在教學啟示與建議上,理論探索與實證不足;第六,較關注英語論說語篇研究,對漢語論說語篇研究相對匱乏。因此,論說語篇仍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2023-08-13 03:45:29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1:00:51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57:01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2025-05-22 10:54:45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2025-05-22 10:51:12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8:48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45:57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2:15
近五年(2010~2014)來對日漢語教學研究綜述2023-08-10 17:22:55
淺論形式邏輯對語言研究的作用2023-08-18 08:17:18
中國喜劇小品中幽默語言的語用分析2023-08-13 08:33:37
近五年(2010~2014)來對日漢語教學研究綜述2023-08-10 17:22:55
淺論形式邏輯對語言研究的作用2023-08-18 08:17:18
中國喜劇小品中幽默語言的語用分析2023-08-13 08:33:37
精品文章
- 1小語界的四位大學教授:田本娜、楊..2023-08-15 11:38:18
- 2碩士學位論文中的人稱指示語研究2023-08-11 19:56:19
- 3論“把”字句動詞掛單問題及對對外..2023-08-13 06:50:50
- 4《漢字形義分析字典》中的象形、指..2023-08-23 00:36:40
- 5詞匯語用視角下的詞類活用研究2023-08-12 12:14:10
- 6婁底市婁星區水洞底鎮方言聲調的演變2023-08-11 16:09:31
- 7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變音及其文..2023-08-11 00:28:24
- 8外國學習者漢語作為第二語言語用習..2023-08-23 13:46:38
- 9漢語教師志愿者跨文化適應研究綜述2023-08-11 06:42:20
- 10近二十年來國內論說語篇研究綜述2023-08-25 12:05:00
圖文推薦

內蒙古高考500至530分左右可以上什么大學
時間:2025-05-22 10:39:38
內蒙古醫科大學對比河北環境工程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
時間:2025-05-22 10:36:19
湖南高考歷史565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時間:2025-05-22 10:32:43
湖北民族大學法學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時間:2025-05-22 10:28:5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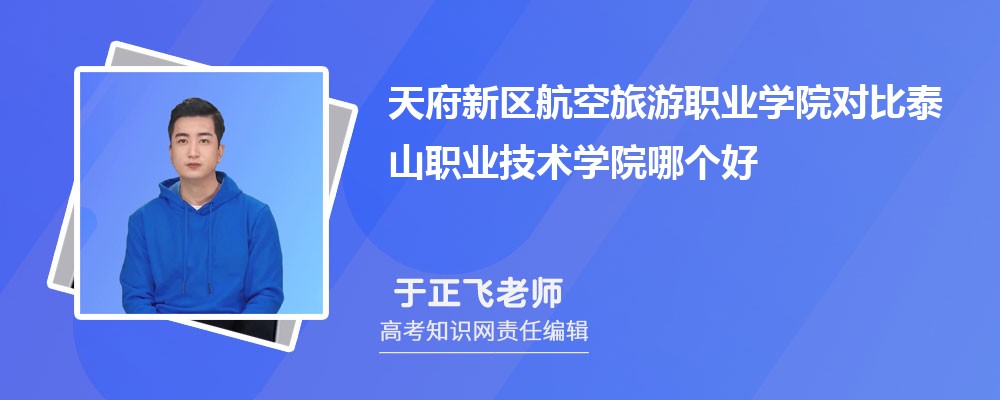
天府新區航空旅游職業學院對比泰山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
時間:2025-05-22 10:25:03
石家莊人民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對比湄洲灣職業技術學院哪..
時間:2025-05-22 10:2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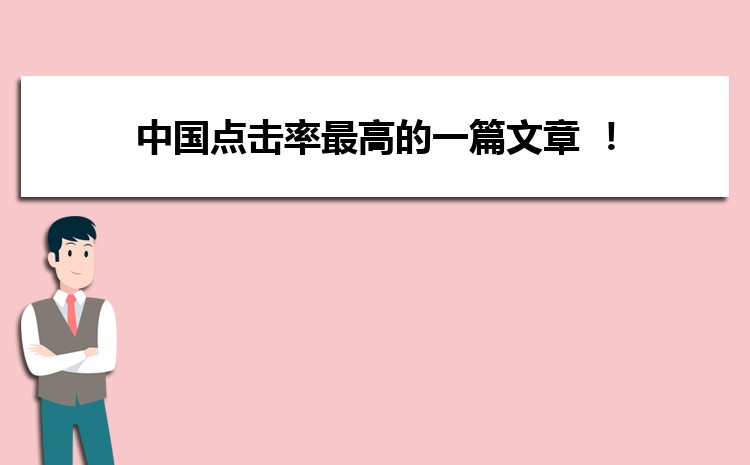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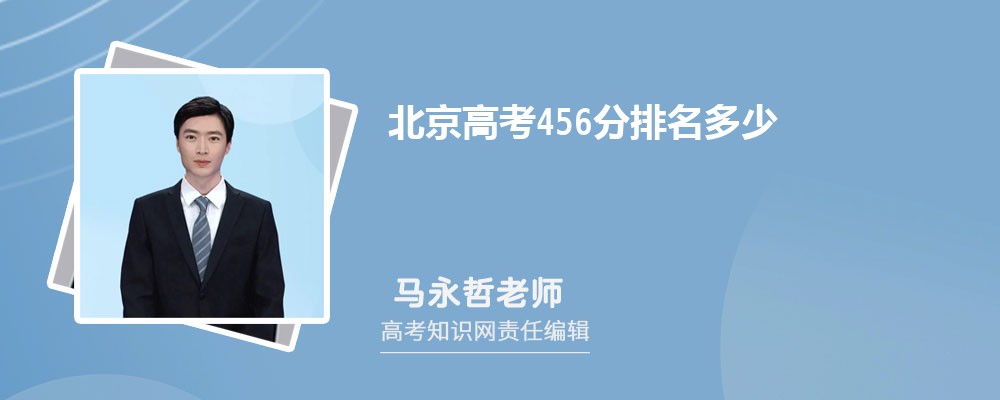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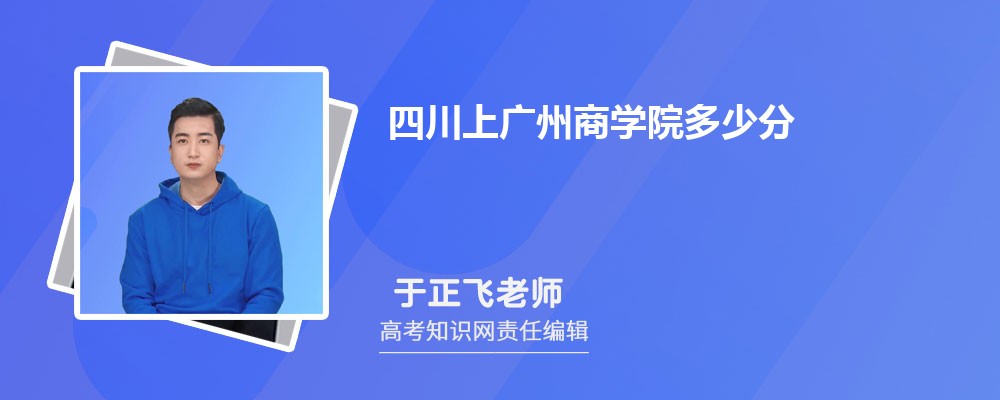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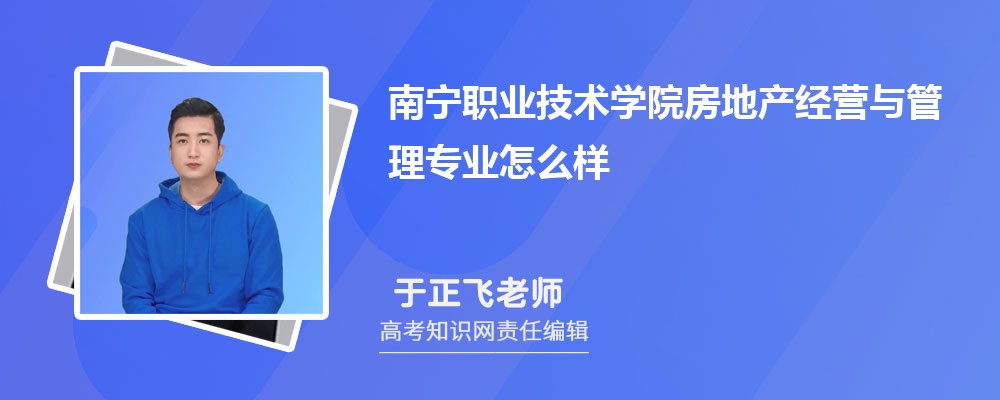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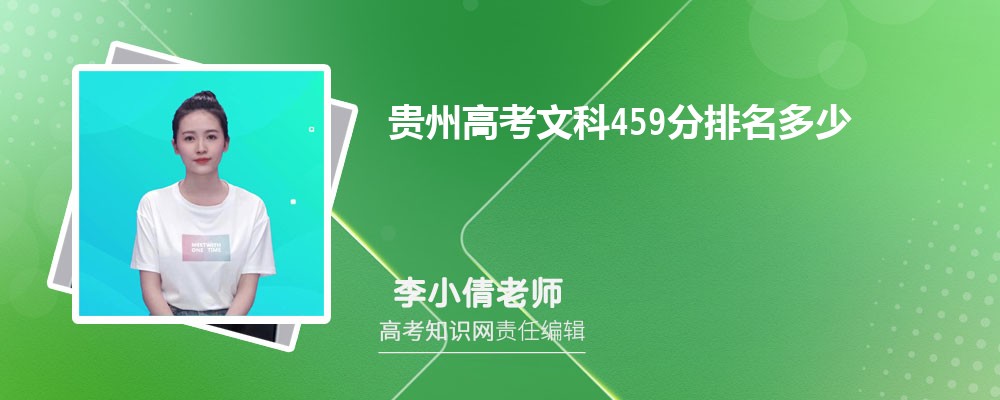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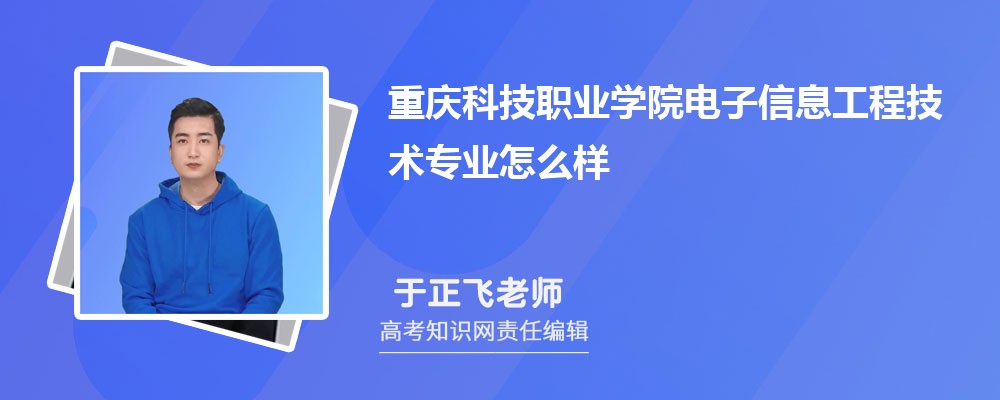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近五年(2010~2014)來對日漢語教學研究綜述
近五年(2010~2014)來對日漢語教學研究綜述 淺論形式邏輯對語言研究的作用
淺論形式邏輯對語言研究的作用 中國喜劇小品中幽默語言的語用分析
中國喜劇小品中幽默語言的語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