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教師要知曉課文之用
更新時間:2023-08-25 16:51:01 高考知識網 www.pvszdiiu.cn張一山老師是江蘇省特級教師、南京市名師工作室主持人、南京市創意寫作課程基地主持人、江蘇師范大學特聘專家。他的《你的學生愛讀語文教材嗎》一文可商榷處甚多,有的言說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語文教學常識,違背了語文教學的規律。因為張一山有專家、名師等頭銜,其言說不單有一定的影響力,還可折射當下語文教育界的另一種生態。為了發揮語文專家、名師的指導、示范和引領作用,防范某些“名家、名師”的誤導,筆者不揣淺陋,冒昧與張老師商榷,并恭請語文教育界的名師、專家們指教。
張老師說到他上高一第一堂語文課時碰到的一件乎不可思議的事:
以北宋理學家邵雍的《山村詠懷》來說,學生在小學一年級就會背誦,即便是今天的課堂上學生也依然能清清楚楚地朗誦出:“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當我把這首詩寫在課堂上的時候,問學生這首詩的題目是什么?作者是誰?是哪個朝代的?作者為什么要寫這首詩?學生們一頭霧水,眼睛可憐巴巴地望著我,希望從我的口里得出答案。??我只得一一“告訴”他們。
張一山就《山村詠懷》向學生提出一連串問題,可“學生們一頭霧水,眼睛可憐巴巴地望著我,希望從我的口里得出答案。”張老師為什么就不多想一下學生為什么會這樣呢?若使用的是人教版語文教材,他面前的學生或許都學過這首詩,但那是在小學一年級上學期學完漢語拼音后的識字第一課,課文的題目是《一去二三里》,不叫《山村詠懷》;課文也沒介紹詩的作者是誰、是哪個朝代的。查閱人教社《教師教學用書》,只說是一首童謠,也沒提供張老師所知的信息。查錢鐘書的《宋詩選注》,未收錄邵雍的詩;查閱人民文學出版社北大教授張鳴選注的《宋詩選》,雖收錄了邵雍的四首詩,但無《山村詠懷》;查中華書局出版的《邵雍集》,也無《山村詠懷》;通過網絡搜索,關于《一去二三里》的文本有三個,作者有北宋的邵雍、元代的徐再思和明代的王道。人教社的《教師教學用書》沒有介紹作者,或許事出有因。張老師既然要向高中生介紹《山村詠懷》的作者,必須是已成定論的知識,而非存疑之說。即使是定論,然他所提的諸多問題,不僅高中生“一頭霧水”,就是大學中文系畢業生也未必能回答。因為現在全國大學中文專業普遍使用的袁行霈主編的高校教材《中國文學史》只字未提邵雍。我們應該看到,小學語文教材編輯選用這首詩,并不是要讓學生知道“作者為什么要寫這首詩”,而是用這首詩呈現《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第一學段的教學內容,作為小學一年級語文教學讀、認、寫、背的材料。即能根據拼音朗讀、背誦這四句詩、認得“一去二三里四五六七八九十”這十二個字;能按筆順會寫“一二三”三個筆畫少的字。若老師按照教材的要求,讓學生能讀、認、寫、背如上內容,也就功德圓滿、實現這一課的教學目標了。不是有許多一線語文教師追求“一課一得”嗎,對學習識字第一課的小學生而言,能“得”這么多,夫復何求!聯系教材編輯意圖和小學一年級學情,張老師若是要一年級的語文課必須告訴他的那些“答案”,那就是置學段目標和學情于不顧,典型的躐等、嚴重地超標了。
其實,張老師只要略知語文課程與教學論知識,課后能多想一個為什么,就不會苛求學生和大驚小怪了。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奧蘇伯爾說:“假如讓我把全部教育心理學僅僅歸納為一條原理的話,那么,我將一言以蔽之:影響學習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學生已經知道了什么,要探明這一點,并應據此進行教學。”作為高中語文教師,若要把握高中語文課應該教什么,就必須知道小學、初中的語文課已經教了什么,學生已經知會了什么;還必須注意到有的課文放在不同的學段應該教什么、編入不同的教學單元必須教什么。
課文是根據國家語文教育政策(主要是《語文課程標準》)選入語文教材的文章和文學作品。入選的方式有全文、片段(節選)、經編輯刪改后的全文或片段、還有編輯自創自編的課文。入選課文還包括單元提示、課前提示、注釋、思考與練等語文要素。課文是文選型語文教材的主要構件,是承載語文教學內容、實現語文教學目標的主要載體或憑借。語文教材中的不少課文,是可以放在不同學段的,學段不同,教學內容也就不一樣。一篇課文,不是老師想教什么就教什么,必須受制于學段目標與內容、選入的單元、選文的文體屬性、具體的學情。同一篇課文,尤其是經典課文,具有多重功能。王榮生通過梳理分析葉圣陶、夏?尊、朱自清等選文類型的理論與實踐,發現和總結了課文功能的發揮方式,即定篇、例文、樣本、用件和引子。盡管有的課文具有多重功能,但在教學實踐中,只能結合所在的學段、單元以及具體的學情,選擇某一種功能,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不能多管齊下。這些最基本的常識,已成為語文教育界的公共知識產品,作為一個合格的語文教師,不可不知。我們注意到,張老師在文中指摘他所使用的語文教材選文和選文的組合存在降低學段水準、忽略學情等問題,但其言說顧此失彼、執于一端,難以讓人信服。原因或許是他不知曉課文之用。多重對話是新一輪語文課改的一個重要理念,其中一重對話就是教師與教科書編者的對話。而要確保對話的有效性,就必須知曉課文之用。不僅如此,要摒棄憑經驗的自以為是的教學、想當然似的隨意教學、面面俱到的天女散花般教學,也必須知曉課文之用。我們很難想象一個不知課文為何物和課文之用的語文教師,有何資格談論語文教育?又如何實施正常的語文教學?
張老師還談到了這首詩的寫作手法、抒發的感情和“背后的意義”:
《山村詠懷》這首詩,作者從煙村寫到亭臺,從亭臺寫到花,物象由大到小,可以看出作者是由遠到的描寫的。作者描寫的是山村的景象,表達的是對山村喜愛之情。我讓學生們把花換成蒼蠅、換成垃圾,我想告訴學生,如果換成這樣的意象,這首詩就不再產生美感了。而這首詩卻常常被用來談論讀書的境界。
邵雍是北宋著名的理學家。他的這首詩表層意思很簡單,但背后的意義很深遠,要從進入理學視野的角度來審視。作為北宋五子之一,邵雍要說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深入地讀書,你的理學境界只能停留在“煙村”的層面上。什么是 “煙村”?就是迷迷蒙蒙,什么都看不清。而如果你認真讀書、真正思考了,你的讀書就進入了“亭?”的境界。而讀書的最高境界就是讀出了“花兒”的心境。這“花兒”的境界就是看到了書中的美,看到了作者的情操,看到作者的審美判斷和審美價值。這樣看來,邵雍的《山村詠懷》其實表達了在理學道路上讀書的三境界??“煙村”“亭臺” “花兒”。
這節文字,張老師是在具體解讀這首詩,觸及這首詩的教學內容,如寫作手法、抒發的感情、“背后的意義”等。但讀后難免給人以“六經注我”、強制闡釋之嫌,為什么“煙村”“就是迷迷蒙蒙,什么都看不清”?難道釋為升起裊裊炊煙的四五家村莊就不通?升起炊煙的村莊,難道就是迷迷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經查,此詩的另一個版本是“一去二三里,山村四五家。門前六七樹,八九十枝花”,“山村”“樹”“花”又表達了什么境界?恕我直言,即使張老師的解讀正確,選擇的教學內容可取,也只能供初高中語文課選用。若用于小學一年級,似無“可取之處”。因為小學一年級學生很難理解接受。確定教學目標,選擇教學內容,必須恪守學段目標、顧及學情。針對語文教學“鐵路警察各管一段”、見一課上一課、簡單低效重復和躐等等現象,筆者曾特別強調語文教學內容的整體觀、層次性、銜接性、目的性和針對性,語文教學內容的確定應該“瞻前而不超前,顧后但不滯后”,即立足所教的學段,做好本學段該做能做的分內之事,為后一學段的教學打好基礎。欲達此目的,就必須了解后一學段的教學內容,才不致盲目超前。同時,還必須了解前一學段的教學內容,以保持前后學段教學內容的銜接,防止簡單低效的重復。某市一重點小學一年級語文教師,要求剛入小學幾天的孩子抄寫她布置的作業題。她有的孩子不會抄便叫來家長,質問他們的孩子為什么不會寫字。當她獲悉這些不會寫字的孩子都來自公辦幼兒園時,聲色俱厲地痛斥公辦幼兒園太不負責任,竟然不教孩子寫字,可謂理直氣壯義正辭嚴。殊不知,幼兒園并沒有承擔教會孩子寫字的教學任務。國家有關部門明令禁止幼兒園小學化,教育部頒布的《3-6歲兒童學習與發展指南》對5?6歲兒童書寫教育目標是“會正確書寫自己的名字”“寫畫時姿勢正確”,其教育建議也僅是“鼓勵幼兒學習書寫自己的名字”。倘若這位老師知道前一學段的教學內容,還會理直氣壯義無反顧地要求孩子和他們的家長配合她嚴重超前嗎?其實,要不犯類似的常識性錯誤也不難。一是研讀《語文課程標準》,文件已把各學段的目標和內容說得一清二楚了;二是把前后學段的教材找來讀讀,就可大致知道自己所教學段該做什么了。這應該是每一個語文教師必須知道的程序性教學知識,是備課環節必做的常規動作。可現今不少執教前面學段的老師大多懶得瞻前,而執教后面學段的老師也不屑后顧。張老師給高一學生講邵雍的《山村詠懷》時,若先翻閱一下小學一年級語文書,或許就不會對學生的一頭霧水而莫名驚詫了。
《你的學生愛讀語文教材嗎》一文可商榷的不止上述兩處。譬如指導學生閱讀食指的《相信未來》,說至少要讀20遍才能讀懂。結果這位同學讀了40遍才發現這首詩的結構奧秘。要求學生多讀,似乎也無可厚非。因為多讀多背多寫多練,幾乎成了從古至今的語文學習的秘籍、寶典,但必須指出的是,如果一個語文老師只會要求學生多讀,只會“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之類的語文學習格言,技止此耳,而無“憤”“悱”之際的啟發,不能適時地授之以漁,就與魯迅描述的“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①的舊式語文教育沒有兩樣,在今天就是不合格的語文教師。如果只要“多”就能教好學好語文,其他科目的老師也可以兼上語文課,甚至根本不需要老師教,學生只要完成基本的識字任務,完全可以自學。學生要讀20遍才懂,但有了語文老師的教,只需三五遍就能讀懂,這才是語文老師的專業本領和真功夫。君不見,凡語文教材上要求學生會寫的字詞、必背的課文,有的語文教師就是簡單粗暴地采取“多”的手段解決問題的。一個字或詞語,學生要抄寫幾十甚至上百遍,仍不會寫而被罰抄的遍數更是驚人!要求背誦的課文,也是簡單地要求不斷地讀、背、抄,舍此而別無良策。這樣的語文課,讓學生望而生畏、毫無興趣!殊不知,盡管質量要有必要的數量保證,但漢字書寫和課文背誦是可以教的!教師完全可以通過有效的教學以減少學生簡單重復的機械操練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們還必須看到,如果讓小學一年級學生讀邵雍的《山村詠懷》,無論讀多少遍,恐怕也讀不出張老師讀出的“背后的意義”。即使張老師告訴學生,學生也不一定懂。因為“多”,既不單指一次性的簡單數量重復,還包括學生有了一定知識積累后不同學段的重讀,乃至人生不同階段再讀而產生的新感受、獲得的新感悟。孫紹振先生堪稱當今語文教育界的文本解讀大家,可他解讀余華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十多年后才發現自己當初的“感悟不夠深刻”。②大家尚且如此,我們又何必強求學生在某一?段把一篇課文、尤其是經典課文完全讀懂呢?又如,張老師說他研讀朱自清的《背影》發現了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父親行為的不檢點、交卸差使與祖母的死有聯系。張老師應該明白“父親行為的不檢點”是《背影》文本外而非文本內的信息,我們無論讀多少遍是絕不會發現這個隱秘信息的。倘若語文老師在中學語文課堂上向學生介紹《背影》中父親行為不檢點等背景知識以顯示自己的多知,或許已背離中學語文《背影》一課的教學目標,有違教材編輯的意圖。
進入21世紀,語文教育界可謂流派紛呈、名家輩出、群星璀璨、光環炫目。不少一線普通語文教師,尤其是新入職的語文教師紛紛主動向名家名師們學習,以提高自己的教學業務水。但我們在學習時可要倍加小心,千萬別被某些名家名師的光環所迷惑。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修訂專家組召集人、部編本語文教材總主編溫儒敏說,語文學科文章數量之多,在各個學科中是首屈一指的,但大多是止于經驗的低水重復③。全國著名的語文課程論專家王榮生說:“我國語文教育研究中的‘語文知識問題,……摻雜了數不清的胡說八道。”④他雖然說的是語文知識領域的問題,但在語文教育研究的其他領域也不乏胡說八道的現象。某知名語文教學期刊刊發的《經典論文應是“六性”的完美結合》一文就是典型一例。“六性”乃文學性、邏輯性、學科性、批判性、廣泛性、建設性,作者以一師范大學教授發表的一篇語文教研文章為佐證和孤證,論證該教授的文章因具備“六性”且是“六性”的完美結合,所以是經典論文。此文堪稱典型的自設標準、信口開河、胡亂吹捧。因為稍有科研常識和經歷的人都知道,文學性、批判性、廣泛性并非論文的必備屬性,孤證是科學研究的大忌,“經典”是要接受實踐檢驗、時間過濾和學界認可的。可就是這么一篇經不起質疑甚至不值一駁的俗爛之文,竟能在知名的語文教學期刊發表,竟能博得被贊譽者的笑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這個最不缺名家名師且各領風騷沒幾天、信息海量般增長、眾語喧嘩的“亂花漸欲迷人眼”時代,最可靠的辦法或許是:一是研讀有定評的大家著述。回望上世紀,胡適、葉圣陶、夏?尊、黎錦?、朱光潛、朱自清、周作人、阮真等前輩有關語文教育的著述,即使在互聯網的今天,也仍有不少“真經”;二是轉益多師;三是要有質疑的頭腦。通過百度獲悉,張一山老師擁有名師、專家等頭銜,新見頻出,著述也不少,傳經布道的機會較多,故本文不是針對張老師個人,而是有感于語文教育界比較普遍的“張一山”現象。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2023-08-13 03:45:29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1:00:51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57:01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2025-05-22 10:54:45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2025-05-22 10:51:12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8:48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2025-05-22 10:45:57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2025-05-22 10:42:15
正確處理初中語文統編教材閱讀教學的三種關系2023-08-23 06:48:51
中小學教師用好助學系統確定教學內容2023-08-26 19:48:40
強化教師的文體意識 培養學生的文體思維2023-08-21 12:14:50
2018全國兩會提案關于個稅改革最新新聞解讀2023-08-13 15:23:45
2019全國兩會提案關于工資改革最新新聞解讀2023-08-16 17:32:35
沒有文學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2023-08-25 21:36:23
精品文章
- 1營造語境,靈活考查學生的語文能力與..2023-08-21 12:38:18
- 2基于自主學習的高中語文課堂診斷研究2023-08-25 12:30:52
- 3欣賞語言文字 品味思想情趣2023-08-27 08:40:43
- 4中考古詩詞畫面描述題的解法探析2023-08-27 05:15:07
- 5淺析小學語文教學中師生之間的有效..2023-08-14 19:09:46
- 62018新版部編初中語文教材解析2023-08-25 20:09:20
- 7基于學生立場的高中語文閱讀教學策略2023-08-22 16:42:18
- 8基于閱讀期待的猜讀法在實用文教學..2023-08-19 21:34:35
- 9比事見義與《左傳?晉公子重耳出亡》2023-08-24 23:06:49
- 10如何上好語文的第一堂課2023-08-23 02:54:04
圖文推薦

內蒙古高考500至530分左右可以上什么大學
時間:2025-05-22 10:39:38
內蒙古醫科大學對比河北環境工程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
時間:2025-05-22 10:36:19
湖南高考歷史565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時間:2025-05-22 10:32:43
湖北民族大學法學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時間:2025-05-22 10:28:5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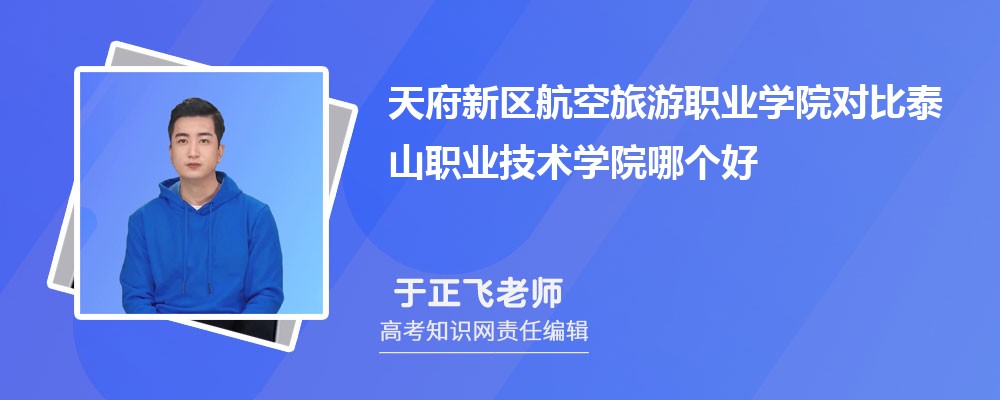
天府新區航空旅游職業學院對比泰山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
時間:2025-05-22 10:25:03
石家莊人民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對比湄洲灣職業技術學院哪..
時間:2025-05-22 10:2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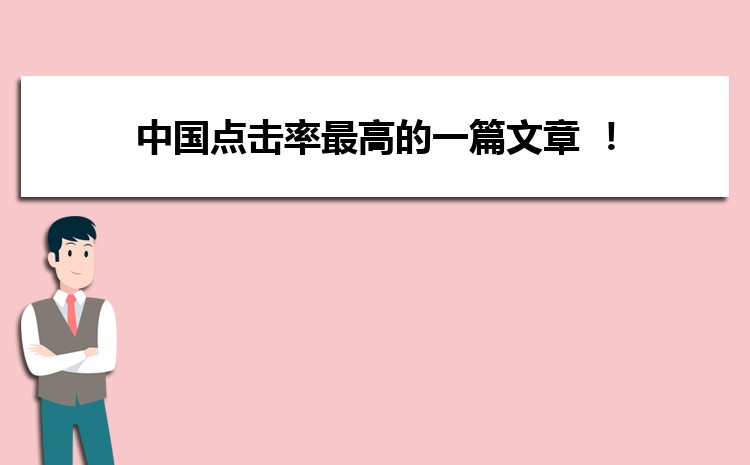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
中國點擊率最高的一篇文章 !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理科347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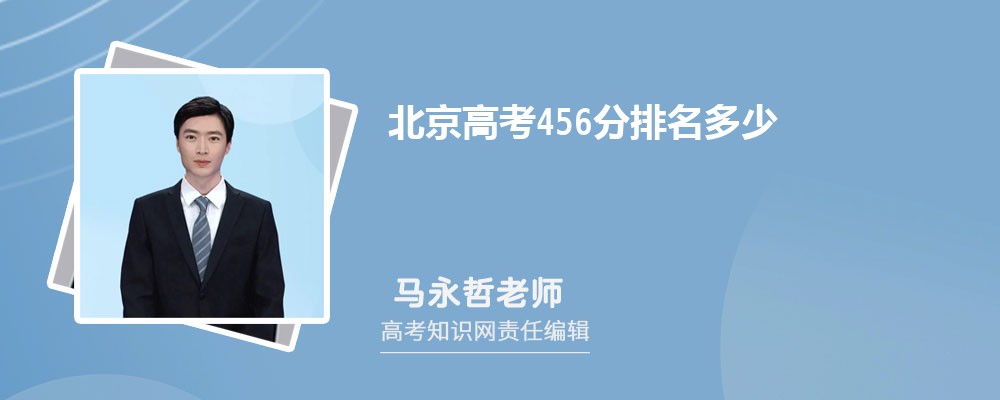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北京高考456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
濟南職業學院對比遼寧機電職業技術學院哪個好 附分數線排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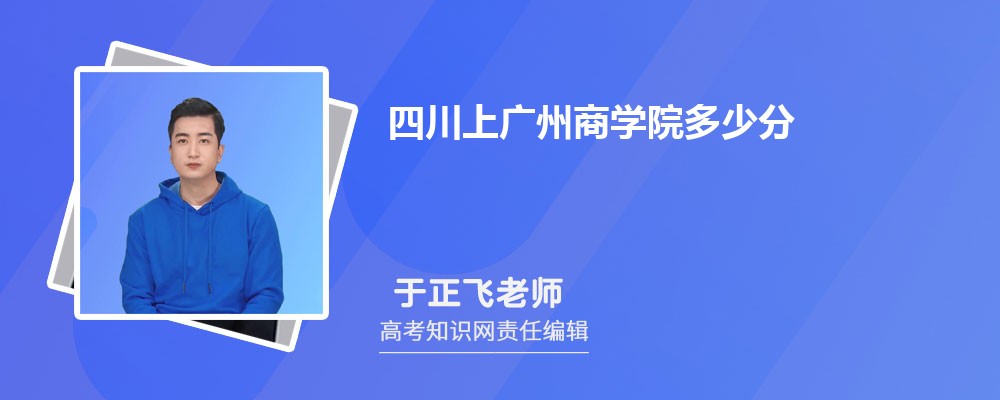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
四川上廣州商學院多少分 分數線及排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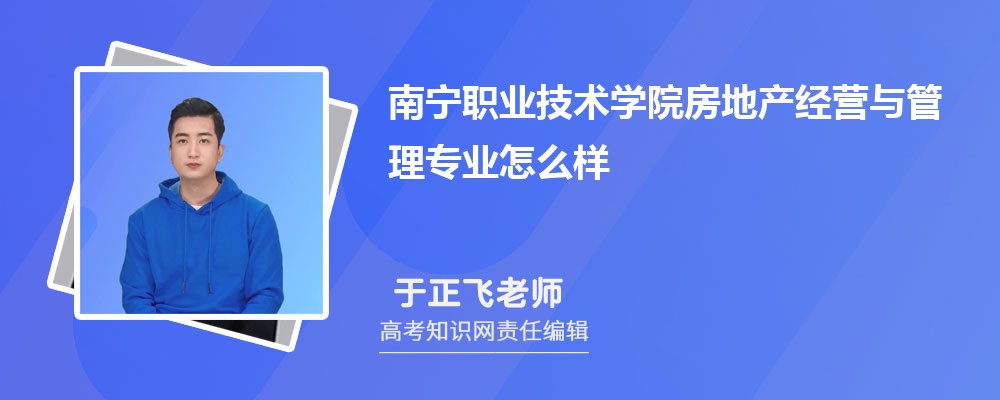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南寧職業技術學院房地產經營與管理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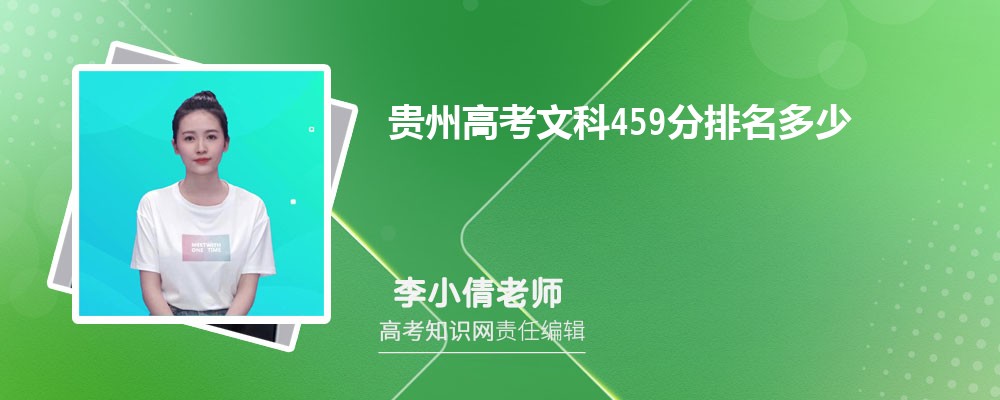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
貴州高考文科459分排名多少 排名多少位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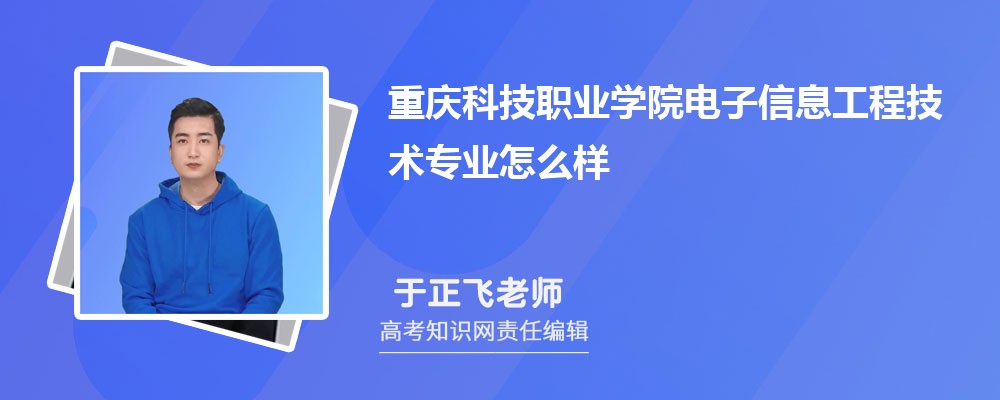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重慶科技職業學院電子信息工程技術專業怎么樣?錄取分數線多少分 正確處理初中語文統編教材閱讀教學的三種關系
正確處理初中語文統編教材閱讀教學的三種關系 中小學教師用好助學系統確定教學內容
中小學教師用好助學系統確定教學內容 強化教師的文體意識 培養學生的文體思維
強化教師的文體意識 培養學生的文體思維 2018全國兩會提案關于個稅改革最新新聞解讀
2018全國兩會提案關于個稅改革最新新聞解讀 2019全國兩會提案關于工資改革最新新聞解讀
2019全國兩會提案關于工資改革最新新聞解讀 沒有文學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沒有文學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